作者:李二河岔
2023/10/11发表于:第一会所
是否首发:是
字数:11,030 字
他的囚徒姑娘以及媳妇和嫂子们以后展演着自己的光臀和裸乳,循循踽踽地
穿行过了广大的山岭、原野,和很多村镇,她们在所有公众清晰的认知底下,像
一群婊子一样人尽可夫。婊子姑娘和媳嫂也在这场行几百里,觅万千夫的长途旅
程当中,收到了触及身心的教育和改造。她们总是显出麻木、恍惚、或者恐惧谄
媚参半的卑贱神情,她们的奶房日渐败落,屁股枯肃尖峭,而更进一步的变化呈
现出了零星散发的大趋势。如果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女人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腰腹
正在悄然变得沉重和壮大,她恐怕的确遭遇到了更进一步堕落的悲惨命运。她应
该已经像母畜一样受精,在很多强制的交配之后终于接受为敌族的兵士和人民们
孕育杂种。没有一个怀孕女囚能够得到减缓责任的区别对待,她们继续纤毫毕现
地面对公众展示了完整的生理周期,她们暴露出的便便大腹既招摇,又笨拙,可
以唤起男人们的另类兴趣,或者某种自豪,同时广而告之自己的肉体已经沦丧而
且叛降的羞耻感。一个被敌人操大了肚子的战士婊子也要继续勉力承付起脚镣的
沉重和手铐的禁制,她在分娩以前一直都会继续被迫着为许多嫖客提供许多的性
生意。
有时候一念而起,不亦乐乎。男人有时候留驻在他巡游队伍的宿营地里等待
入夜。他的囚徒姑嫂们正在休憩。女人们的赤身都在木笼的栅栏后边彼此相倚坐
卧,有些女人有意但也许是无意地环拥住了她们的同伴,她和她的同伴的赤身依
偎在一起。她们的赤身形销骨立。男人留驻在靠近牛车木笼的地方,观看了那些
战士出身的女人在她们乐享过长期婊子命运以后变成的卑贱样子。有一些皮面裹
覆住瘦骨,有一些瘦骨横斜错落地勾搭堆叠,她们总是那样任由着自己的四肢松
弛懈怠地开张和伸展。囚笼中有时出现的一个,或者更多几个凸露昭彰的壮大肉
肚引人注目,它们在嶙峋支离的破败场景中圆肥丰隆地安身立命的姿态奇异而且
莫测。男人也观看了许多横陈在车底板上的光腿,和一些朝向车沿以外茫然无依
地翻翘了起来,憔悴平乏,肮脏黑暗的光裸脚掌。
他想她们的精神和身体应该都已经崩溃。实际上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她们
的屄也已经崩溃。他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她们的生殖器了。所以那些肚子和他肯定
没有关系。他以后还受人敬赠了一件肥美白皙的胡女礼物,他觉得羯胡女人那一
大条各种去处都生有棕红汗毛的肥白身体很有劲头。当然了,胡女奴隶过得是跟
他一起整天吃羊肉的日子,吃饱了肯定有劲头。他的囚犯女人每天能够分到的吃
食只有一碗麦子麸皮。要是见到哪一位大嫂比较健壮,见天的辛劳见天的很有精
神,那就单挑出来多饿,每过两天只给半碗。除了挨操挨打以外,光是这一个饿
法就能把她们熬到心慌腿软,魂不守舍。说起来瘐病狱中也是当一个囚犯少不得
要尽到的本分,天长日久饿得慌软的人再不该有劲,再不该有想,每天除了吃食
以外不会去想星星和曙光的事。就像猪一样。
那一天他观看到了他的羯族奴隶女人的光脚,走过了月亮底下很白的草。那
天入夜以后的月亮很大。他想,另有一些男人和女人可能也会看向了她的同样泛
白的身体。羯族姑娘那时已经解开了遮身的老虎皮毛,她在住宿营地里随侍主人
的时候早已经习惯了始终都要全身赤露,当然她也习惯了始终都要锁系在她赤手
和光脚中间的那些沉重狼亢的铁镣。总是要被锁系住腕子的两只空拳不能分离到
尺半以外的地方,一个即使出身于胡蛮的姑娘所伸张开的颀长的手掌和手指头仍
然可以是清丽的,她的指尖在舒张的时候分寸宽和,可以在抚摸中顾及到广大的
面积,或者收束得尖锐,不过每当她谨守在驭奴刑具所限定的狭窄范围里操行劳
作的时候,它们的情和形总是表现出很多的沉着和朴素。戴镣的女奴赤身为他打
水洗澡,生火烤肉,以后又为他打开一张游牧人民习用的收放马扎,那件特制的
坐具除了可以折叠起来方便携带,还安装有更高的支架和一副靠背,可以使他万
一打算看向月亮的时候得到背部的支承。当然倚身而坐的感受也会更加舒适。
男人有时候在他一念而起的大月亮夜里,倚坐在一张靠背马扎上观看他的赤
身女奴殴打裸形犯妇们的暴力局面。他很喜欢。他的羯族姑娘也知道他会喜欢。
那天他想打的人是一个可能已经就要临盆的怀孕女人,奴隶姑娘正在走近笼车去
安排打人的事。平常都会有些犯妇女人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特别处分,比较常
用的就是给人反臂戴上背铐,让她多过几天从早到晚都没有手爪可以抓挠的烦难
日子。两手反背的女人就只能沿着笼子底板调派她的屁股和腿,等到了她使用一
对忙活着抠扒的精光脚掌把自己和自己扭摆摇曳着的臃然肉肚,终于能够一锅端
到了笼车边沿,当然没有人帮扶,总算车沿并不太高,背铐的足月孕妇单凭一副
锁系重链的腿脚,颤颤巍巍地摸索了出来能够落地的重心。她在使用自己颀长但
是露骨的瘦削躯体为那一个圆肥丰隆的肚子提供支持的时候,所作出的努力惨淡
坚忍,她也循照着一个裸体犯妇的惯常行迹,在她脚腕上拴系的重链铁镣,还有
另外附加的,始终支撑开她左右踝骨的长杆木棍子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分张开
展了自己膝踝兀凸的长腿,她在自己敞荡的大胯中间展现出了所有搭着瓣的打着
卷的鸡零狗碎,而后她朝向泛月光的白草地里屈膝下跪。每一个被人点着了名字
招出来的犯妇都是要下跪的,跪端庄以后方便挨到正足的打。犯妇们难得梳理的
素面总是乱发纷拂,他的奴隶姑娘一手攥定了妇人整把的头发丝绺,另一幅挥开
的巴掌上边,五指张扬,泼风一样地横扫下去。奴隶姑娘的腕子在她受禁刑具所
限定的尺半之内也可以是凌厉的,妇人憔悴平乏,肮脏黑暗的嘴脸上就会挨受到
一连串正足凌厉的响亮耳光。他的女奴经常随心地抽打犯妇,那些随心完全没有
缘由,只是因为他喜欢看到女人被打脸,她只是打给他看。她也会体贴地站在一
个偏侧的位置上,让自己的主人总是能够将那些挨打女人惨痛混乱地挣扎着的正
脸觑得清楚。
男主后来也在那张犯妇的脸上看到了更进一步的混乱和纠结。女人脸上有时
显露出来的微妙的矛盾关系值得男人玩味。他的赤身的女奴那时已经按照惯例掌
过了裸形犯妇的嘴,她还要按照惯例作弄她的屄。当然她要就近地寻一个可以作
弄的趁手器物也很方便。他们的笼车栅栏上本来就错落零碎地挂有各种拴人脖子
和奶的铜铃、铁球、还有狗链,车开到外面的时候也挂,总是要教车里呆着的和
车外边路过的所有的谁和谁们,没事都能多看几眼。羯奴女孩当时取下来的是一
件尺半的长度,寸许圆周,两端各生一个微翘龟首的铸铁用器,器身周遭铸印有
累累凸露的半圆珠粒,器身的仲部悬垂有两颗浑圆的铃铛。悬铃似乎是一种相关
现实的灵魂模拟,而同样是从器身中间分引出来,总共两副四条可以拴扣的系链
则是一种用作实操的便宜安排,既然它是一个供给两人同时使用的性玩具,它的
确应该能够一次性地环围住两副女人腰身。整件器物的用处当然并无可疑,女孩
一手揽住跪立的孕妇后腰,一边将那支龟首连带着珠粒摇移旋拧,直往她的身体
里边怼入进去,孕妇有一些凝眉和喘息。女孩再将系链沿顺着那人如同一面皮鼓
样子的大腹底边,从左从右盘绕到后腰地方锁扣固定。她再扇她一个嘴巴。她说,
等着!
精赤条条的孕妇军官展露出了很多的羞辱情势,沉默地等在很多敌军男人和
自己率领过的妇女战士们的注视之中。现在更多的军队男人开始参加进来,他们
在征召裸体的妇女战士下车列队的时候既动嘴也动手,更多背铐敞腿的女人都在
场景的侧面跪立成阵。他的奴隶女孩继续担负了耗费体力的繁冗劳动,她在自己
的将军主人舒适地依赖着的靠背马扎,和犯妇军官饱经辱虐沧桑的精赤身体之间,
有条不紊地安装起一座带有底框和支撑横档的木架结构。那副用作支撑女人受奸
的木架在巡游开始以前经过改造,可以拆散捆扎安排马匹运送,也可以使用插销
和榫头重新拼装起来。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犯妇女人喜提了一个臃鼓的大肚子,
近段时间以来她都只能采取仰躺的姿势接受奸淫。有人踢了她的光屁股,要求她
携带上一己肉身之内的,各个可淫可虐的器官自行前往作案现场,背铐敞腿的大
肚子女人现在跪立膝行着抵近了木架,她被人抬高而且分置了胳膊和腿,孤悬了
使用木架横撑的后腰。女人那时的前身荡仰,肚子突兀,后体垂堕不能继,形同
一张反弓。这一次他的奴隶女孩在把女人的腿脚和底座连结到一起的时候,使用
的是可以旋拧收缩的精铁小环,她分别地单锁了女人两只脚下的大拇趾。足趾当
然是一处相比腕骨脆弱很多的支撑点,女人的两只被拴紧到了底座边沿的赤脚飞
流直下,激突的足背神形险恶。他以后确实观阅了一些孤零的大脚拇趾狰狞地戟
指,而其他的趾头痉挛着团聚的邪魅风情。他想,一个反腰、孤悬,而又被束身
在支架上的裸体孕妇,在她分敞的腿胯遭受到连番激烈的冲撞的时候,可能会觉
得脊椎和趾骨都已经断裂,她会在一种自下而上的仰望视界里看到自己沉重壮大
的圆滚肉肚摇曳翩跹的样子,那种体验应该会很有独到之处。当然另有一件更加
重大深切的体验已经直抵了她的血肉纵深,她一定会在顾此失彼的心慌气短中努
力地兼得到许多的痛苦。
从她分敞的腿胯以及装置其中的浑铁杵棒往前。她的女兵姐妹们正在依次,
逐个抵近操演地带。大多都是背铐的女人只能使用她们的私密器具裸裎以待,她
们经过一些游移,摩挲,试探,最终都会凭借着自己敏感柔和的唇瓣成功地捕捉
到架上女胯中间伸挺出来的悍然铁棒,并且珠联璧合一般将它纳入进自己的蜜壶。
铁棒壮大,她们都在非常张狂怒放的蜜壶中体验到了环珠滑移的难以启齿。从旁
监督的军士俯身过来,他在她们的身体夹缝里找到铁杵上牵带的第二副系链,环
围住了第二个人的腰,他将架上和架下的两个女玩家圈禁到了同一场性虐游戏,
他也会使用皮鞭激励她们的性游戏。处在了架下那个位置的性伴需要更主动,她
在赤身捱受鞭打的痛楚中踊跃奋进,她也许是仅凭着一己之力糅合了两副腿胯内
的四片肉唇,迫使它们发生了许多的簇拥和厮磨,两座女人绚烂绽放的门户前庭
几乎都要将杵棒中线安装的浑圆铃球包容了进去,造成了喧哗的鸣响声音时断时
续。每一次都要捅插到底,每一次都要迅疾地抽拔。前边给人身安装双头用具的
时候,拴腰的链子肯定都会留出有余地,可以包容她在那个余地里伶俐地辗转抽
身,她可以通过一种撅屁股抖腿的滑稽姿势操作自己腿胯内的汩汩唇瓣,充分地
含抿摩挲过生铁铸就的蓬勃的龟首。男人那时已经起身走到了木架旁边,其实他
自己的身体上下也都没有穿着衣服,他只是觉得夜草有点湿凉,一时没有脱掉骑
马时候穿的皮靴。倚靠着立柱的男人向下观阅了女人肮脏黑暗的脸,还有他的羯
族姑娘白皙分展的赤裸肩臂。奴仆姑娘跪立在木架的另外一侧,她正在努力地往
女人的唇齿之间安装一具精铁口环,她也使用一些环绕过女人脸颊的绳索系紧了
口环。男人往前转过立柱,跪低的羯族奴女攥紧了束身在架上的女人后脑的长头
发。她对准他的胯下推举起来她的合不拢的嘴。
奴隶女孩推送的节奏宽急有度。她操纵那副女人的喉舌容纳,含蕴,收束,
吞咽了他。她迫使她的软咽被一条汹涌闯荡的鸡巴急骤地磨合。女孩娴熟地操纵
着妇人的嘴脸在裸男的胯下吞吐萦回,不过她也会在宽缓的时候融入自己。女孩
有时低头献舌舔舐在男女两身交合的中间环节,她先用舌头环绕过他,而后又暂
且搁置了女人亲自吞咽他。男人在两个婊子的喉舌之间徜徉了一些回合。而在刑
架的另外一面,赤身赤足的妇女战队正在皮鞭的驱赶下依次,逐个,并且周而复
始地巡行,她们努力克服着肢体间的连锁重负,使用极限淫具轮番虐待了她们裸
形受缚的妇女长官的性器,以及她们自己的性器。后来他带着他的奴隶女孩返回
到马扎附近,把那一口婊子长官的嘴留给了他的军士兄弟。兄弟们在轮番奸污她
的软咽的时候也都还算卖力。男人以后使用羯奴的身体打发掉了更多的激情,而
她跪在他的腿间舔干净终于开始逐渐松弛了下去的男人的肉。女孩以后乖巧地为
他脱掉了马靴。她问,主人想要女奴把她领来,舔一回主人的脚吗。他有时候想,
他那天只是没想。他懒洋洋地说了一句,鞋吧。
后来她被几个军士兄弟挟制住胳膊拉扯到了马扎对面。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她
从刑架上拆解了下来,没有管她嘴里卡着的,和两腿中间扎着的东西,当然她现
在更脏了,满脸淋漓泛滥的那种脏法,兵们往她头上浇了一桶凉水,才把她清洗
出了几分能够见人的眉目。女人跪在草地上被他看了一阵眉目。羯奴女孩这一次
走过去的时候提着他的高腰马靴,她把马靴扔到了女人的脏脸上。皮鞋和皮鞋沿
着女人的溜圆肚子,打滚蹦跳着落下地去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有一个带着鞭子的
兵挥手抽了她的背脊,反铐跪伏的女人拱高了她的背脊,她在草中轮流搬动起来
两个膝头,摇移跌撞地追随着鞋。后来女人吐露出舌头的软尖开始清洁鞋子的皮
面。她应该是很努力地克服了扩嘴口环的阻碍,才能够做到那样又灵活、又长久
地使动舌头。他的兵们还会往她的头顶和拱高了的赤裸背脊上扔下更多肮脏的皮
靴和便鞋。
女俘虏们使动舌头为自己的征服者舔干净鞋是她们经常要做的事。他今天没
让她挨着个地舔干净他的大兵们的光脚丫子,他想她应该感念不尽他的恩情。更
不用说他本来可以让她继续呆在木头架子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娱乐他那一整支
队伍里的所有公牛和公马。队里的公牛马们一路以来食髓知味,除了喜欢母的牛
马,也不是一定不能喜欢母的人。或者就是撮合不同物种间的爱慕之情总要有些
引导和调教,既费时,又费事,反正折腾半夜就是看一条特别粗犷的大马鸡巴插
在女人的小屄里边,特别豪放地杵捣那种事,他们也不是一定都要每晚招出自己
去待见。他的羯族姑娘以后一直都像一个好姑娘一样趴跪在底下舔他的腿脚,她
也像个好姑娘一样一直没有忘了还要操心着主人的鞋。姑娘有时候从他的腿边直
起腰来并不是打算歇一口气,她不在乎戴着脚镣多走几个来回,她就是要凑近过
去多看一眼人家那边一直都在努力地舔着鞋的口活儿。反正每回过去总能找出一
个她觉得没有侍弄干净的地方,每找出一处,狠抽两个嘴巴。以后奴隶姑娘继续
跪舔她的主人,军官婊子继续跪舔所有征服了她的大兵们的鞋。一般他会在这样
的好月夜里慢慢打起了瞌睡,兵们会把人犯拖回笼子,也会把他扶进一座行军用
的帐篷,他们还会给自己搭一座更大些的帐篷睡到里边。问题当然并不在于这些
平常都要做的事。
聚了众的女人全伙坦荡裸裎而且彼此瞩目,她们兼容并蓄着同一条粗铁鸡巴
互相奸淫的事比较没羞没臊。他不太确定女人们的心里该是平常还是不平常。他
觉得她们一边推己一边及人,互相撩拨完了这样一场内囊都尽了上来的骚情以后,
再挨挤到车子的木笼里一起过夜的时候,总该有点没法说的羞惭、愧疚,惴惴嗫
嚅着不好互对眼神。要是哪个女人在她总是劈开了的腿岔中间伸挺出来一杆粗铁
棒子,她大概也会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在一众的同伴注视底下安置好自己。
那件东西附带的系链环腰以后可以上锁,反正只要兵们没有费事给她拆解,她和
笼子里的女犯也就没人能够拆解。在她那个又堵,又撑,总有许多生硬的珠突滚
滚地碾磨在软薄膣腔里的奇特感受,肯定也会让一个女人难以控制自己生态和心
态的诸方面平衡。撅着光屁股给兵们舔一堆鞋的事也不好平衡。现在的问题就是
婊子们在那些从人生朝向着肉畜蜕变的不平衡里,仍然沉着镇定地给出了她们的
独特的回应。
正如男人现在已经知道,她们很可能就在奸辱结束以后的那些下半夜里,有
条不紊地谈论了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军事和人文话题。她们在处理比较大量数
据的时候应该是采用了分解任务的方法,指定不同的个人负责记忆不同地区的各
项要素。所以她们会在各种可用的时间里进行细致的交流,并且将所有分散获取
的零星消息传递给特定的人,她们也会在以后的路程中经常地默念那些要素加深
记忆。简单直白地看,实际上是那个已经沦落成为了敌人囚徒和奴隶的妇女统帅
在她自己的牢笼中建立了临时的情报指挥中心,她在应对完毕了自己每一天都要
承担的奴隶娼妓的工作以后,返回到指控中心继续领导她的妇女战士开展了情报
的收集和整理。男人想象了一些女人们的赤身在木笼的栅栏后边彼此相倚坐卧的
样子,她们敞露着堕坠的干瘪乳房,在车厢底板上横陈光腿,一边叙述了山岭中
间可以通行的垭口方位,河流的盈枯季节,以及边城围墙的高阔尺寸那样的事,
那种情境奇特而且荒谬,就像是他发现自己圈禁的性奴在半夜换上一双透明的鞋
子,坐在南瓜里前往参加一场国王舞会一样,他甚至会觉得那十分地具有唤起男
人欲望的淫荡性。
他和他的性奴在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得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他看到她们
安静地乘坐笼车上路。而女人知道她们都将面对很大的死亡可能性,所以她们也
许在安排使用人脑记忆住同一处地区的资讯的时候,指定了两个人以上的互相备
份。怀孕的女人更容易死。女的大活人们露天制造出小活人的过程既禁忌,又张
扬,她们没法避开男人兴趣盎然的注意力。一个赤身裸体,反臂背铐,并且在踝
间系带有脚镣重链的大肚子女人,她在流汗和喘气中辗转挣拧两只光脚的样子表
现出了很多的禁忌和很多张扬,而男人们兴趣盎然,他们趁机试验了更多更加刻
薄的兴趣方向。使用细韧的麻绳拴紧女人奶头,把一个孕妇牵领在牛车后面长途
跋涉的想法检验了女性神经的敏感性。每一匹女人奶房上的,每一头囫囵肉骨朵
上蕾蕊重叠,感触尖稚,这些都被麻绳毛糙扎刺的编绞筋股收住口、较住劲,直
往前边一路勒索而去,它使女人遭受到的刺痛酷烈,它也使女人遭受的撩拨隐隐
约约。一个被勒被撩到了心慌腿软,面孔潮红,一边努力搬弄可能已经酥麻了的
腿脚筛糠一样走路的光身女人,也很能遭受男人调笑。女人的两只奶头支楞楞地
牵挂在她胸前一尺以外的凌空地方,两匹抻长抻紧绷着的奶房上边,青紫的筋管
回环涨放,骑着马的兵们从上往下多看两眼忍不住就要调笑,都说姐姐你这两个
奶子的吃相好生有趣,便像是路边店里的兰州师傅作弄出来的拉面一样。
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都被拴过奶头跟车走路。等到有谁被人搞大了肚子,她
再被拴到车子后边,再走,她就会知道大着肚子的自己很快就会走不动。女人凝
视了自己两只光赤脚板的许多游移、畏缩,和趴窝,它们努力要在路面上扒持住
最后一些浮砂的样子缠绵悱恻。女人在那些实在难以为继的最后关头可能是嘶声
哀叫过的,她可能是在求饶,但是她其实知道求饶从来没有用,所以她也许就是
疼得不得不叫。她看到天空后退,砂石飞升起来撞歪,撞憋了自已笨重的肚子,
她的软肉在她的眼睛底下抽尖、绽裂,两道继续往前飞掠了出去的影子应该就是
本来拴住她的奶头的两边绳扣。她也会听到周围马背上哄然发出的许多爆笑声。
有些时候一念而起。不知其何往何止,覆水不好收拾。不收手地玩下去就得
要见到更多血了。平常那些能够给人见血的铁签子和尖钩,都是随手挂在笼子栅
栏上晃悠着给人看的,等到了需要在现场实际地行使起来,一种是把那一支尖头
的签子贴根横穿过一头奶房,再穿一头奶房,挨扎女人的那些吱哇乱叫当然都是
情理之中了,扎通以后再给两奶夹缝里横戳着的签杆系一条铁链,等到了上路当
然就是使用这条铁链把人拴在牛车后边。其实既然身处在了他们这个乱世的时,
和混战的地,这种往人奶上扎通了洞眼,系进绳索领人光身游街的事,本来就是
不论官兵还是盗匪,平常都会行使的手段。若果遇到要将那一个反贼或者对头杀
一个全家,不妨也就趁便将他一家门当中的全体女眷一个一个地去衣穿胸,先游
街,再活剐,可以趁便立住了狂霸酷屌的杀伐声威,大概也能让自家兄弟和驻地
的人民在心里得到一些抓抓挠挠的奇怪念想。
对于那些围观了穿胸的女人跟在牛车后边跑路的士兵兄弟,可能总会觉得念
想里边还是差了一把两把抓挠。铁器太直太狠。不管前边拉扯着的是牛轮、马腿,
还是人手,一拉一扯之间女人满胸腔子里大概都只剩下了泼天也似的疼痛,肯定
不能像勒奶头的刺毛麻筋那样连带着撩人。虽说依照着天演而论起来,女人天生
便都拥有一颗骚贱内心的事实已经广为芸芸直男所知道,不过一条直接捅进女人
肉里的粗铁棒子确实并不能造成性唤起。女人走到后来也要跌跤,每跌一次都会
将那个贯通了两奶的伤口拉扯到更大,多跌几次还会爬不起来。再要想法子就是
用车把人顶住,教她没有地方可跌。
其实他们试过收紧女人胸间的系链挂到笼子的顶框上去,那时的女人前身平
倚住笼壁,她整一条身体的重量就都可以凭着洞穿两团奶肉的裂口向上提吊,她
就不会再摔倒了。当然到了那种时候观瞻难免显得凄厉。女人的胸乳受力向上,
头脸后仰,乱发自然飘拂,她的全条赤身和木笼的栏壁中间紧紧抵住的只是她那
一幅浑圆的肉肚,反正她的腿脚已经基本不再管用,它们在零碎虚弱地跟出几个
跨步以后,就会被拖成了脚踝反转,趾掌向天的颠覆样子,拖行的脚背遭受砂石
消磨,也会在路上留下细碎血肉。女人的呜咽有气无力。而更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穿通了的胸,那里边的血肉也在消磨。单靠着生肉的那一点筋滞劲道并不能把一
整个女人吊挂在车子上走到太远,承受着重量的铁签迟早会完全地分割开所有人
肉人皮的阻碍,形神险恶地破壁而出。
他们就是在想法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人类肩背上的肌肉特别有韧
劲的事。幸运的是女人类的背肌特性也是一样。他们以后改装了笼车,在木笼顶
上安装了一根打横伸出到车轮以外八九尺远的木头棍子,从那以后他们每当遇到
有怀孕的女犯婊子羊水破裂,就会使用一对尖钩分别地勾穿她的后背肌腱,将她
牵吊在长棍下边。当时他们还没有发展出以后使用的那种给人背上钉环的精巧办
法,他们只是会给女人的脖子挂上更多的木板招牌、铜的铃铛和铁铸的双头鸡巴,
迫使她的重心前移,保持住一种虽然耸背,但是低俯下肩膀和脑袋盲目向前冲撞
的姿势。而且她的两脚接地。所以她虽然在一场又一场临盆的阵痛发生起来的时
候疼得抽搐打跌,形色狰狞,并且拼尽了所有可能残存下的力气惨叫,但是牛车
没有停顿,她的身体仍然悬坠、碾压在她的两只痉挛得像是吞下了钓钩的泥鳅那
样扭来扭去的光赤脚板上,使动每一只脚,走完了每一步路。在她的那些几乎是
无穷无尽地使动了下去的所有光赤脚板之间,除了一如既往的连篇重镣,还有总
是撑顶在两踝中间的横档,她在永远敞荡开张的腿胯中间娩出了她的胎儿,在一
脚板又一脚板的痉挛和抽搐中从头开始,激烈地,漫漫地,一寸一寸娩出了胎儿
的完整的身体。她一鼓作气生产出了很多黏连和血污的东西拖累在可以被人看到
的腿胯中间。头脸低俯的女人朝向自己身下颠倒地分辨了那些东西,它还没有睁
眼,手脚蹬踢,她像一个妈妈一样看了它最后一眼。后来有人叫停了牛车,不过
他们并不是要从挂钩底下解开女人,他们只是蹲身到女人的脚下割断了黏连的牵
绊。而后他们会继续上路。
女人在行路中生产下的那些不知道属于谁的孩子都会被简单地抛弃在路边。
反正那肯定不会是他的问题。新生在草原和沙中的孩子们是稀缺的资源,途经的
游牧部落也许会捡走他们,给予用心的照料抚养,但是也许在很多天里一直没有
人途经。这是一种扔出骰子的概率游戏。每一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扔骰子的游戏。
牛车和它侧伸出的横木底下垂悬的尖钩是一场胜率很低的轮盘赌局,那些被钩穿
了脊背,悬在底下一边走一边生的女人,大多都会死。实际上他们有时再也没有
解开那些女人,他们会让一个产妇的体重继续悬坠、碾压在她自己的光脚板上,
拽镣,分腿,反臂,在分娩以后的两天,三天,甚至更多天中一步一步走死自己。
他在分娩完毕的军官妇人继续负镣分腿,俯首弓背地跟车走过了两天以后,
吩咐卸除掉她肉里的铁钩,把她送回笼子里去休养身体,他甚至让人给她的伤口
涂抹了金疮药。当然他不是想要帮助那个女人从她自己的人生赌局中胜出。无论
如何,杀死或者不杀死一些看起来已经堕落成为母牲口的东西,并不应该造成很
多的未来改变。他当时只是想要她暂且可以多活几天,可以继续遭受到更多更加
深重的苦。
所以就是现在的未来确实已经改变。男人在他以后的很多早晨走过院中回廊
的时候,总是会有些迷惑不解地,感觉到了共历时空可能存在的各向相异性。早
晨的院子很安静,院中铺石的前庭里生有几棵事不关己的女贞树。年前京城大将
军从他那里带走了所有剩下的中原女人,这座院子就是女人们以后的集体居住地。
这里的四面院墙围定了一处适当的私密空间,空间里有周正的中厅,平实的厢房,
厢房里有床。它看起来确实适合一些女人住在里边接待前来搞她们的男人。除了
一些很高等级的场合需要亲自送上门去让人搞,她们应该就是在这里操办了大多
数按照传说可以通过连接性器而祈使福运的神奇活动。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看起来
也很适合编写一些秘密报告。如果女人得到哪一个祈福男人的帮助,她就可以躲
在厢房里写一晚上的字,记录下所有那些她们了解观察到的消息,如果男人继续
付钱,还可以给她买到更多晚上。她们多半也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把消息传递了出
去。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的社会关系最终都是可以交易的买卖关系,中
原女人们的性关系也是一样。每一个京城居民都可以找到这座院子,按照官方的
定价付钱,而后选择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一间厢房里去,连接彼此的性器官。所以
如果不是案犯们自己招供的话,他和京城大将军大概没法找到那个男人。
现在这里当然已经不再操办那些祝你幸福的生意。官方发布的公告是中原敌
国的女人已经离开京城,开始了她们第二次扬威巡游。而他按照京城将军的指派
着手处理她们的案件,他每天都会前来院中工作。沿墙整排厢房前边的花坛里正
在张扬开放的重瓣菊花是各向相异的,它们的容颜明亮但是寂静无声。他身边的
羯族女奴着落在铺石上的赤足也很安静。女奴脚镣的回响始终延续,但是因为它
的孤立、外在、和单调,可以不计入到安静中来。他们在走过整排紧闭的厢房门
扇的时候,一直可以听到一些缭绕的女人呜咽和喘息。他知道她们一直在挨打,
她们在很多使人死去活来的疼痛中,和男人寻求事件真相的逻辑理性共历了那些
时空。
他的奴隶姑娘紧走两步赶向前方去为他开门。他看到了迎门的后墙底下,从
一个较高的位置俯首、全幅、正对的女人身体。女人的赤臂合并竖举,她的手腕
被捆绑的绳索朝向屋顶牵吊得更高。女人低垂的面目前边遮挡有一些散乱的头发,
女人前倾的裸胸上垂堕的奶房疏寡,绵长,薄肉宽皮,两匹奶房浓色的软苞底下
各自拴挂有一个黑铁秤砣。每一个骑跨在一座木马的尖峭脊背上的女人,都会得
到一个憋扭,支离,裂解,模样和相貌难以名状的性器官。女人阴唇结聚处的肉
埠因为承受着重压而鼓凸了出来,她那一骨朵皱皮都遮挡不住了的蒂头肥圆臃肿,
红中泛紫的晶莹样子几乎是珠圆玉润的,她的肿胀的阴蒂被刺入了尖针,阴蒂的
根基里结扎有细绳,绳子的另头也都使用秤砣配重。这样一个重物侧挂在了木马
斜边,它也像摘花一样拈长,捻歪了女人阴蒂的肿大肉头。女人的屁股整体中立。
女人使用自己一左一右的两条光赤长腿紧紧地夹拢住了木马的倾斜侧壁,她的两
支壁立的大脚拇指根里各自拴挂的三块青砖足够沉重,能够帮助她保持住自己光
赤屁股的痛苦中立。
女人骑跨了一整个晚上的木马,就是一座平常用来摧折妇女刑犯的木马。安
装在四支高腿上的马身侧壁自下向上,从宽到窄,倾斜着支撑起来的尖峭脊梁横
行而且兀立。它深入地楔进并且扩张开一条软嫩缝隙的能力没有疑问。女人的性
器就是那条缝隙。女人自己的体重和脚趾头下的青砖重量一起,帮助她在一支坚
硬的木头楔子上极限地深切,扩张,并且充分地削磨蹂躏了自己的性器官。实际
上她已经从自己的肉唇肉户中压榨出了许多红白混杂,四处流泻开去的浆液和水。
她可能想象过一棵大白菜一样包裹紧密的、多汁多水的屄,被牛或者马那样的大
动物咬嚼开了的样子。她的遍布于女人性器软膜上的所有丝缕感触都已经极致地
扩张开放,可以使她同时体验到尖利、钝重、疾速划掠和持续弥漫的所有疼痛,
她应该已经疼得四分五裂。
男人想,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重新回来,阻挡在他的道路前边。人生是一群
猪,最终会在每一个远方遇见命定的木薯。我们可以有时地想象上树,但是我们
真正迷恋的仍然只是泥土。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做他命定要做的事。
2023/10/11发表于:第一会所
是否首发:是
字数:11,030 字
他的囚徒姑娘以及媳妇和嫂子们以后展演着自己的光臀和裸乳,循循踽踽地
穿行过了广大的山岭、原野,和很多村镇,她们在所有公众清晰的认知底下,像
一群婊子一样人尽可夫。婊子姑娘和媳嫂也在这场行几百里,觅万千夫的长途旅
程当中,收到了触及身心的教育和改造。她们总是显出麻木、恍惚、或者恐惧谄
媚参半的卑贱神情,她们的奶房日渐败落,屁股枯肃尖峭,而更进一步的变化呈
现出了零星散发的大趋势。如果她们之中的某一个女人惊恐地意识到自己的腰腹
正在悄然变得沉重和壮大,她恐怕的确遭遇到了更进一步堕落的悲惨命运。她应
该已经像母畜一样受精,在很多强制的交配之后终于接受为敌族的兵士和人民们
孕育杂种。没有一个怀孕女囚能够得到减缓责任的区别对待,她们继续纤毫毕现
地面对公众展示了完整的生理周期,她们暴露出的便便大腹既招摇,又笨拙,可
以唤起男人们的另类兴趣,或者某种自豪,同时广而告之自己的肉体已经沦丧而
且叛降的羞耻感。一个被敌人操大了肚子的战士婊子也要继续勉力承付起脚镣的
沉重和手铐的禁制,她在分娩以前一直都会继续被迫着为许多嫖客提供许多的性
生意。
有时候一念而起,不亦乐乎。男人有时候留驻在他巡游队伍的宿营地里等待
入夜。他的囚徒姑嫂们正在休憩。女人们的赤身都在木笼的栅栏后边彼此相倚坐
卧,有些女人有意但也许是无意地环拥住了她们的同伴,她和她的同伴的赤身依
偎在一起。她们的赤身形销骨立。男人留驻在靠近牛车木笼的地方,观看了那些
战士出身的女人在她们乐享过长期婊子命运以后变成的卑贱样子。有一些皮面裹
覆住瘦骨,有一些瘦骨横斜错落地勾搭堆叠,她们总是那样任由着自己的四肢松
弛懈怠地开张和伸展。囚笼中有时出现的一个,或者更多几个凸露昭彰的壮大肉
肚引人注目,它们在嶙峋支离的破败场景中圆肥丰隆地安身立命的姿态奇异而且
莫测。男人也观看了许多横陈在车底板上的光腿,和一些朝向车沿以外茫然无依
地翻翘了起来,憔悴平乏,肮脏黑暗的光裸脚掌。
他想她们的精神和身体应该都已经崩溃。实际上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她们
的屄也已经崩溃。他已经很久没有使用她们的生殖器了。所以那些肚子和他肯定
没有关系。他以后还受人敬赠了一件肥美白皙的胡女礼物,他觉得羯胡女人那一
大条各种去处都生有棕红汗毛的肥白身体很有劲头。当然了,胡女奴隶过得是跟
他一起整天吃羊肉的日子,吃饱了肯定有劲头。他的囚犯女人每天能够分到的吃
食只有一碗麦子麸皮。要是见到哪一位大嫂比较健壮,见天的辛劳见天的很有精
神,那就单挑出来多饿,每过两天只给半碗。除了挨操挨打以外,光是这一个饿
法就能把她们熬到心慌腿软,魂不守舍。说起来瘐病狱中也是当一个囚犯少不得
要尽到的本分,天长日久饿得慌软的人再不该有劲,再不该有想,每天除了吃食
以外不会去想星星和曙光的事。就像猪一样。
那一天他观看到了他的羯族奴隶女人的光脚,走过了月亮底下很白的草。那
天入夜以后的月亮很大。他想,另有一些男人和女人可能也会看向了她的同样泛
白的身体。羯族姑娘那时已经解开了遮身的老虎皮毛,她在住宿营地里随侍主人
的时候早已经习惯了始终都要全身赤露,当然她也习惯了始终都要锁系在她赤手
和光脚中间的那些沉重狼亢的铁镣。总是要被锁系住腕子的两只空拳不能分离到
尺半以外的地方,一个即使出身于胡蛮的姑娘所伸张开的颀长的手掌和手指头仍
然可以是清丽的,她的指尖在舒张的时候分寸宽和,可以在抚摸中顾及到广大的
面积,或者收束得尖锐,不过每当她谨守在驭奴刑具所限定的狭窄范围里操行劳
作的时候,它们的情和形总是表现出很多的沉着和朴素。戴镣的女奴赤身为他打
水洗澡,生火烤肉,以后又为他打开一张游牧人民习用的收放马扎,那件特制的
坐具除了可以折叠起来方便携带,还安装有更高的支架和一副靠背,可以使他万
一打算看向月亮的时候得到背部的支承。当然倚身而坐的感受也会更加舒适。
男人有时候在他一念而起的大月亮夜里,倚坐在一张靠背马扎上观看他的赤
身女奴殴打裸形犯妇们的暴力局面。他很喜欢。他的羯族姑娘也知道他会喜欢。
那天他想打的人是一个可能已经就要临盆的怀孕女人,奴隶姑娘正在走近笼车去
安排打人的事。平常都会有些犯妇女人遭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特别处分,比较常
用的就是给人反臂戴上背铐,让她多过几天从早到晚都没有手爪可以抓挠的烦难
日子。两手反背的女人就只能沿着笼子底板调派她的屁股和腿,等到了她使用一
对忙活着抠扒的精光脚掌把自己和自己扭摆摇曳着的臃然肉肚,终于能够一锅端
到了笼车边沿,当然没有人帮扶,总算车沿并不太高,背铐的足月孕妇单凭一副
锁系重链的腿脚,颤颤巍巍地摸索了出来能够落地的重心。她在使用自己颀长但
是露骨的瘦削躯体为那一个圆肥丰隆的肚子提供支持的时候,所作出的努力惨淡
坚忍,她也循照着一个裸体犯妇的惯常行迹,在她脚腕上拴系的重链铁镣,还有
另外附加的,始终支撑开她左右踝骨的长杆木棍子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分张开
展了自己膝踝兀凸的长腿,她在自己敞荡的大胯中间展现出了所有搭着瓣的打着
卷的鸡零狗碎,而后她朝向泛月光的白草地里屈膝下跪。每一个被人点着了名字
招出来的犯妇都是要下跪的,跪端庄以后方便挨到正足的打。犯妇们难得梳理的
素面总是乱发纷拂,他的奴隶姑娘一手攥定了妇人整把的头发丝绺,另一幅挥开
的巴掌上边,五指张扬,泼风一样地横扫下去。奴隶姑娘的腕子在她受禁刑具所
限定的尺半之内也可以是凌厉的,妇人憔悴平乏,肮脏黑暗的嘴脸上就会挨受到
一连串正足凌厉的响亮耳光。他的女奴经常随心地抽打犯妇,那些随心完全没有
缘由,只是因为他喜欢看到女人被打脸,她只是打给他看。她也会体贴地站在一
个偏侧的位置上,让自己的主人总是能够将那些挨打女人惨痛混乱地挣扎着的正
脸觑得清楚。
男主后来也在那张犯妇的脸上看到了更进一步的混乱和纠结。女人脸上有时
显露出来的微妙的矛盾关系值得男人玩味。他的赤身的女奴那时已经按照惯例掌
过了裸形犯妇的嘴,她还要按照惯例作弄她的屄。当然她要就近地寻一个可以作
弄的趁手器物也很方便。他们的笼车栅栏上本来就错落零碎地挂有各种拴人脖子
和奶的铜铃、铁球、还有狗链,车开到外面的时候也挂,总是要教车里呆着的和
车外边路过的所有的谁和谁们,没事都能多看几眼。羯奴女孩当时取下来的是一
件尺半的长度,寸许圆周,两端各生一个微翘龟首的铸铁用器,器身周遭铸印有
累累凸露的半圆珠粒,器身的仲部悬垂有两颗浑圆的铃铛。悬铃似乎是一种相关
现实的灵魂模拟,而同样是从器身中间分引出来,总共两副四条可以拴扣的系链
则是一种用作实操的便宜安排,既然它是一个供给两人同时使用的性玩具,它的
确应该能够一次性地环围住两副女人腰身。整件器物的用处当然并无可疑,女孩
一手揽住跪立的孕妇后腰,一边将那支龟首连带着珠粒摇移旋拧,直往她的身体
里边怼入进去,孕妇有一些凝眉和喘息。女孩再将系链沿顺着那人如同一面皮鼓
样子的大腹底边,从左从右盘绕到后腰地方锁扣固定。她再扇她一个嘴巴。她说,
等着!
精赤条条的孕妇军官展露出了很多的羞辱情势,沉默地等在很多敌军男人和
自己率领过的妇女战士们的注视之中。现在更多的军队男人开始参加进来,他们
在征召裸体的妇女战士下车列队的时候既动嘴也动手,更多背铐敞腿的女人都在
场景的侧面跪立成阵。他的奴隶女孩继续担负了耗费体力的繁冗劳动,她在自己
的将军主人舒适地依赖着的靠背马扎,和犯妇军官饱经辱虐沧桑的精赤身体之间,
有条不紊地安装起一座带有底框和支撑横档的木架结构。那副用作支撑女人受奸
的木架在巡游开始以前经过改造,可以拆散捆扎安排马匹运送,也可以使用插销
和榫头重新拼装起来。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犯妇女人喜提了一个臃鼓的大肚子,
近段时间以来她都只能采取仰躺的姿势接受奸淫。有人踢了她的光屁股,要求她
携带上一己肉身之内的,各个可淫可虐的器官自行前往作案现场,背铐敞腿的大
肚子女人现在跪立膝行着抵近了木架,她被人抬高而且分置了胳膊和腿,孤悬了
使用木架横撑的后腰。女人那时的前身荡仰,肚子突兀,后体垂堕不能继,形同
一张反弓。这一次他的奴隶女孩在把女人的腿脚和底座连结到一起的时候,使用
的是可以旋拧收缩的精铁小环,她分别地单锁了女人两只脚下的大拇趾。足趾当
然是一处相比腕骨脆弱很多的支撑点,女人的两只被拴紧到了底座边沿的赤脚飞
流直下,激突的足背神形险恶。他以后确实观阅了一些孤零的大脚拇趾狰狞地戟
指,而其他的趾头痉挛着团聚的邪魅风情。他想,一个反腰、孤悬,而又被束身
在支架上的裸体孕妇,在她分敞的腿胯遭受到连番激烈的冲撞的时候,可能会觉
得脊椎和趾骨都已经断裂,她会在一种自下而上的仰望视界里看到自己沉重壮大
的圆滚肉肚摇曳翩跹的样子,那种体验应该会很有独到之处。当然另有一件更加
重大深切的体验已经直抵了她的血肉纵深,她一定会在顾此失彼的心慌气短中努
力地兼得到许多的痛苦。
从她分敞的腿胯以及装置其中的浑铁杵棒往前。她的女兵姐妹们正在依次,
逐个抵近操演地带。大多都是背铐的女人只能使用她们的私密器具裸裎以待,她
们经过一些游移,摩挲,试探,最终都会凭借着自己敏感柔和的唇瓣成功地捕捉
到架上女胯中间伸挺出来的悍然铁棒,并且珠联璧合一般将它纳入进自己的蜜壶。
铁棒壮大,她们都在非常张狂怒放的蜜壶中体验到了环珠滑移的难以启齿。从旁
监督的军士俯身过来,他在她们的身体夹缝里找到铁杵上牵带的第二副系链,环
围住了第二个人的腰,他将架上和架下的两个女玩家圈禁到了同一场性虐游戏,
他也会使用皮鞭激励她们的性游戏。处在了架下那个位置的性伴需要更主动,她
在赤身捱受鞭打的痛楚中踊跃奋进,她也许是仅凭着一己之力糅合了两副腿胯内
的四片肉唇,迫使它们发生了许多的簇拥和厮磨,两座女人绚烂绽放的门户前庭
几乎都要将杵棒中线安装的浑圆铃球包容了进去,造成了喧哗的鸣响声音时断时
续。每一次都要捅插到底,每一次都要迅疾地抽拔。前边给人身安装双头用具的
时候,拴腰的链子肯定都会留出有余地,可以包容她在那个余地里伶俐地辗转抽
身,她可以通过一种撅屁股抖腿的滑稽姿势操作自己腿胯内的汩汩唇瓣,充分地
含抿摩挲过生铁铸就的蓬勃的龟首。男人那时已经起身走到了木架旁边,其实他
自己的身体上下也都没有穿着衣服,他只是觉得夜草有点湿凉,一时没有脱掉骑
马时候穿的皮靴。倚靠着立柱的男人向下观阅了女人肮脏黑暗的脸,还有他的羯
族姑娘白皙分展的赤裸肩臂。奴仆姑娘跪立在木架的另外一侧,她正在努力地往
女人的唇齿之间安装一具精铁口环,她也使用一些环绕过女人脸颊的绳索系紧了
口环。男人往前转过立柱,跪低的羯族奴女攥紧了束身在架上的女人后脑的长头
发。她对准他的胯下推举起来她的合不拢的嘴。
奴隶女孩推送的节奏宽急有度。她操纵那副女人的喉舌容纳,含蕴,收束,
吞咽了他。她迫使她的软咽被一条汹涌闯荡的鸡巴急骤地磨合。女孩娴熟地操纵
着妇人的嘴脸在裸男的胯下吞吐萦回,不过她也会在宽缓的时候融入自己。女孩
有时低头献舌舔舐在男女两身交合的中间环节,她先用舌头环绕过他,而后又暂
且搁置了女人亲自吞咽他。男人在两个婊子的喉舌之间徜徉了一些回合。而在刑
架的另外一面,赤身赤足的妇女战队正在皮鞭的驱赶下依次,逐个,并且周而复
始地巡行,她们努力克服着肢体间的连锁重负,使用极限淫具轮番虐待了她们裸
形受缚的妇女长官的性器,以及她们自己的性器。后来他带着他的奴隶女孩返回
到马扎附近,把那一口婊子长官的嘴留给了他的军士兄弟。兄弟们在轮番奸污她
的软咽的时候也都还算卖力。男人以后使用羯奴的身体打发掉了更多的激情,而
她跪在他的腿间舔干净终于开始逐渐松弛了下去的男人的肉。女孩以后乖巧地为
他脱掉了马靴。她问,主人想要女奴把她领来,舔一回主人的脚吗。他有时候想,
他那天只是没想。他懒洋洋地说了一句,鞋吧。
后来她被几个军士兄弟挟制住胳膊拉扯到了马扎对面。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她
从刑架上拆解了下来,没有管她嘴里卡着的,和两腿中间扎着的东西,当然她现
在更脏了,满脸淋漓泛滥的那种脏法,兵们往她头上浇了一桶凉水,才把她清洗
出了几分能够见人的眉目。女人跪在草地上被他看了一阵眉目。羯奴女孩这一次
走过去的时候提着他的高腰马靴,她把马靴扔到了女人的脏脸上。皮鞋和皮鞋沿
着女人的溜圆肚子,打滚蹦跳着落下地去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有一个带着鞭子的
兵挥手抽了她的背脊,反铐跪伏的女人拱高了她的背脊,她在草中轮流搬动起来
两个膝头,摇移跌撞地追随着鞋。后来女人吐露出舌头的软尖开始清洁鞋子的皮
面。她应该是很努力地克服了扩嘴口环的阻碍,才能够做到那样又灵活、又长久
地使动舌头。他的兵们还会往她的头顶和拱高了的赤裸背脊上扔下更多肮脏的皮
靴和便鞋。
女俘虏们使动舌头为自己的征服者舔干净鞋是她们经常要做的事。他今天没
让她挨着个地舔干净他的大兵们的光脚丫子,他想她应该感念不尽他的恩情。更
不用说他本来可以让她继续呆在木头架子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娱乐他那一整支
队伍里的所有公牛和公马。队里的公牛马们一路以来食髓知味,除了喜欢母的牛
马,也不是一定不能喜欢母的人。或者就是撮合不同物种间的爱慕之情总要有些
引导和调教,既费时,又费事,反正折腾半夜就是看一条特别粗犷的大马鸡巴插
在女人的小屄里边,特别豪放地杵捣那种事,他们也不是一定都要每晚招出自己
去待见。他的羯族姑娘以后一直都像一个好姑娘一样趴跪在底下舔他的腿脚,她
也像个好姑娘一样一直没有忘了还要操心着主人的鞋。姑娘有时候从他的腿边直
起腰来并不是打算歇一口气,她不在乎戴着脚镣多走几个来回,她就是要凑近过
去多看一眼人家那边一直都在努力地舔着鞋的口活儿。反正每回过去总能找出一
个她觉得没有侍弄干净的地方,每找出一处,狠抽两个嘴巴。以后奴隶姑娘继续
跪舔她的主人,军官婊子继续跪舔所有征服了她的大兵们的鞋。一般他会在这样
的好月夜里慢慢打起了瞌睡,兵们会把人犯拖回笼子,也会把他扶进一座行军用
的帐篷,他们还会给自己搭一座更大些的帐篷睡到里边。问题当然并不在于这些
平常都要做的事。
聚了众的女人全伙坦荡裸裎而且彼此瞩目,她们兼容并蓄着同一条粗铁鸡巴
互相奸淫的事比较没羞没臊。他不太确定女人们的心里该是平常还是不平常。他
觉得她们一边推己一边及人,互相撩拨完了这样一场内囊都尽了上来的骚情以后,
再挨挤到车子的木笼里一起过夜的时候,总该有点没法说的羞惭、愧疚,惴惴嗫
嚅着不好互对眼神。要是哪个女人在她总是劈开了的腿岔中间伸挺出来一杆粗铁
棒子,她大概也会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在一众的同伴注视底下安置好自己。
那件东西附带的系链环腰以后可以上锁,反正只要兵们没有费事给她拆解,她和
笼子里的女犯也就没人能够拆解。在她那个又堵,又撑,总有许多生硬的珠突滚
滚地碾磨在软薄膣腔里的奇特感受,肯定也会让一个女人难以控制自己生态和心
态的诸方面平衡。撅着光屁股给兵们舔一堆鞋的事也不好平衡。现在的问题就是
婊子们在那些从人生朝向着肉畜蜕变的不平衡里,仍然沉着镇定地给出了她们的
独特的回应。
正如男人现在已经知道,她们很可能就在奸辱结束以后的那些下半夜里,有
条不紊地谈论了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军事和人文话题。她们在处理比较大量数
据的时候应该是采用了分解任务的方法,指定不同的个人负责记忆不同地区的各
项要素。所以她们会在各种可用的时间里进行细致的交流,并且将所有分散获取
的零星消息传递给特定的人,她们也会在以后的路程中经常地默念那些要素加深
记忆。简单直白地看,实际上是那个已经沦落成为了敌人囚徒和奴隶的妇女统帅
在她自己的牢笼中建立了临时的情报指挥中心,她在应对完毕了自己每一天都要
承担的奴隶娼妓的工作以后,返回到指控中心继续领导她的妇女战士开展了情报
的收集和整理。男人想象了一些女人们的赤身在木笼的栅栏后边彼此相倚坐卧的
样子,她们敞露着堕坠的干瘪乳房,在车厢底板上横陈光腿,一边叙述了山岭中
间可以通行的垭口方位,河流的盈枯季节,以及边城围墙的高阔尺寸那样的事,
那种情境奇特而且荒谬,就像是他发现自己圈禁的性奴在半夜换上一双透明的鞋
子,坐在南瓜里前往参加一场国王舞会一样,他甚至会觉得那十分地具有唤起男
人欲望的淫荡性。
他和他的性奴在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得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他看到她们
安静地乘坐笼车上路。而女人知道她们都将面对很大的死亡可能性,所以她们也
许在安排使用人脑记忆住同一处地区的资讯的时候,指定了两个人以上的互相备
份。怀孕的女人更容易死。女的大活人们露天制造出小活人的过程既禁忌,又张
扬,她们没法避开男人兴趣盎然的注意力。一个赤身裸体,反臂背铐,并且在踝
间系带有脚镣重链的大肚子女人,她在流汗和喘气中辗转挣拧两只光脚的样子表
现出了很多的禁忌和很多张扬,而男人们兴趣盎然,他们趁机试验了更多更加刻
薄的兴趣方向。使用细韧的麻绳拴紧女人奶头,把一个孕妇牵领在牛车后面长途
跋涉的想法检验了女性神经的敏感性。每一匹女人奶房上的,每一头囫囵肉骨朵
上蕾蕊重叠,感触尖稚,这些都被麻绳毛糙扎刺的编绞筋股收住口、较住劲,直
往前边一路勒索而去,它使女人遭受到的刺痛酷烈,它也使女人遭受的撩拨隐隐
约约。一个被勒被撩到了心慌腿软,面孔潮红,一边努力搬弄可能已经酥麻了的
腿脚筛糠一样走路的光身女人,也很能遭受男人调笑。女人的两只奶头支楞楞地
牵挂在她胸前一尺以外的凌空地方,两匹抻长抻紧绷着的奶房上边,青紫的筋管
回环涨放,骑着马的兵们从上往下多看两眼忍不住就要调笑,都说姐姐你这两个
奶子的吃相好生有趣,便像是路边店里的兰州师傅作弄出来的拉面一样。
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都被拴过奶头跟车走路。等到有谁被人搞大了肚子,她
再被拴到车子后边,再走,她就会知道大着肚子的自己很快就会走不动。女人凝
视了自己两只光赤脚板的许多游移、畏缩,和趴窝,它们努力要在路面上扒持住
最后一些浮砂的样子缠绵悱恻。女人在那些实在难以为继的最后关头可能是嘶声
哀叫过的,她可能是在求饶,但是她其实知道求饶从来没有用,所以她也许就是
疼得不得不叫。她看到天空后退,砂石飞升起来撞歪,撞憋了自已笨重的肚子,
她的软肉在她的眼睛底下抽尖、绽裂,两道继续往前飞掠了出去的影子应该就是
本来拴住她的奶头的两边绳扣。她也会听到周围马背上哄然发出的许多爆笑声。
有些时候一念而起。不知其何往何止,覆水不好收拾。不收手地玩下去就得
要见到更多血了。平常那些能够给人见血的铁签子和尖钩,都是随手挂在笼子栅
栏上晃悠着给人看的,等到了需要在现场实际地行使起来,一种是把那一支尖头
的签子贴根横穿过一头奶房,再穿一头奶房,挨扎女人的那些吱哇乱叫当然都是
情理之中了,扎通以后再给两奶夹缝里横戳着的签杆系一条铁链,等到了上路当
然就是使用这条铁链把人拴在牛车后边。其实既然身处在了他们这个乱世的时,
和混战的地,这种往人奶上扎通了洞眼,系进绳索领人光身游街的事,本来就是
不论官兵还是盗匪,平常都会行使的手段。若果遇到要将那一个反贼或者对头杀
一个全家,不妨也就趁便将他一家门当中的全体女眷一个一个地去衣穿胸,先游
街,再活剐,可以趁便立住了狂霸酷屌的杀伐声威,大概也能让自家兄弟和驻地
的人民在心里得到一些抓抓挠挠的奇怪念想。
对于那些围观了穿胸的女人跟在牛车后边跑路的士兵兄弟,可能总会觉得念
想里边还是差了一把两把抓挠。铁器太直太狠。不管前边拉扯着的是牛轮、马腿,
还是人手,一拉一扯之间女人满胸腔子里大概都只剩下了泼天也似的疼痛,肯定
不能像勒奶头的刺毛麻筋那样连带着撩人。虽说依照着天演而论起来,女人天生
便都拥有一颗骚贱内心的事实已经广为芸芸直男所知道,不过一条直接捅进女人
肉里的粗铁棒子确实并不能造成性唤起。女人走到后来也要跌跤,每跌一次都会
将那个贯通了两奶的伤口拉扯到更大,多跌几次还会爬不起来。再要想法子就是
用车把人顶住,教她没有地方可跌。
其实他们试过收紧女人胸间的系链挂到笼子的顶框上去,那时的女人前身平
倚住笼壁,她整一条身体的重量就都可以凭着洞穿两团奶肉的裂口向上提吊,她
就不会再摔倒了。当然到了那种时候观瞻难免显得凄厉。女人的胸乳受力向上,
头脸后仰,乱发自然飘拂,她的全条赤身和木笼的栏壁中间紧紧抵住的只是她那
一幅浑圆的肉肚,反正她的腿脚已经基本不再管用,它们在零碎虚弱地跟出几个
跨步以后,就会被拖成了脚踝反转,趾掌向天的颠覆样子,拖行的脚背遭受砂石
消磨,也会在路上留下细碎血肉。女人的呜咽有气无力。而更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穿通了的胸,那里边的血肉也在消磨。单靠着生肉的那一点筋滞劲道并不能把一
整个女人吊挂在车子上走到太远,承受着重量的铁签迟早会完全地分割开所有人
肉人皮的阻碍,形神险恶地破壁而出。
他们就是在想法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人类肩背上的肌肉特别有韧
劲的事。幸运的是女人类的背肌特性也是一样。他们以后改装了笼车,在木笼顶
上安装了一根打横伸出到车轮以外八九尺远的木头棍子,从那以后他们每当遇到
有怀孕的女犯婊子羊水破裂,就会使用一对尖钩分别地勾穿她的后背肌腱,将她
牵吊在长棍下边。当时他们还没有发展出以后使用的那种给人背上钉环的精巧办
法,他们只是会给女人的脖子挂上更多的木板招牌、铜的铃铛和铁铸的双头鸡巴,
迫使她的重心前移,保持住一种虽然耸背,但是低俯下肩膀和脑袋盲目向前冲撞
的姿势。而且她的两脚接地。所以她虽然在一场又一场临盆的阵痛发生起来的时
候疼得抽搐打跌,形色狰狞,并且拼尽了所有可能残存下的力气惨叫,但是牛车
没有停顿,她的身体仍然悬坠、碾压在她的两只痉挛得像是吞下了钓钩的泥鳅那
样扭来扭去的光赤脚板上,使动每一只脚,走完了每一步路。在她的那些几乎是
无穷无尽地使动了下去的所有光赤脚板之间,除了一如既往的连篇重镣,还有总
是撑顶在两踝中间的横档,她在永远敞荡开张的腿胯中间娩出了她的胎儿,在一
脚板又一脚板的痉挛和抽搐中从头开始,激烈地,漫漫地,一寸一寸娩出了胎儿
的完整的身体。她一鼓作气生产出了很多黏连和血污的东西拖累在可以被人看到
的腿胯中间。头脸低俯的女人朝向自己身下颠倒地分辨了那些东西,它还没有睁
眼,手脚蹬踢,她像一个妈妈一样看了它最后一眼。后来有人叫停了牛车,不过
他们并不是要从挂钩底下解开女人,他们只是蹲身到女人的脚下割断了黏连的牵
绊。而后他们会继续上路。
女人在行路中生产下的那些不知道属于谁的孩子都会被简单地抛弃在路边。
反正那肯定不会是他的问题。新生在草原和沙中的孩子们是稀缺的资源,途经的
游牧部落也许会捡走他们,给予用心的照料抚养,但是也许在很多天里一直没有
人途经。这是一种扔出骰子的概率游戏。每一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扔骰子的游戏。
牛车和它侧伸出的横木底下垂悬的尖钩是一场胜率很低的轮盘赌局,那些被钩穿
了脊背,悬在底下一边走一边生的女人,大多都会死。实际上他们有时再也没有
解开那些女人,他们会让一个产妇的体重继续悬坠、碾压在她自己的光脚板上,
拽镣,分腿,反臂,在分娩以后的两天,三天,甚至更多天中一步一步走死自己。
他在分娩完毕的军官妇人继续负镣分腿,俯首弓背地跟车走过了两天以后,
吩咐卸除掉她肉里的铁钩,把她送回笼子里去休养身体,他甚至让人给她的伤口
涂抹了金疮药。当然他不是想要帮助那个女人从她自己的人生赌局中胜出。无论
如何,杀死或者不杀死一些看起来已经堕落成为母牲口的东西,并不应该造成很
多的未来改变。他当时只是想要她暂且可以多活几天,可以继续遭受到更多更加
深重的苦。
所以就是现在的未来确实已经改变。男人在他以后的很多早晨走过院中回廊
的时候,总是会有些迷惑不解地,感觉到了共历时空可能存在的各向相异性。早
晨的院子很安静,院中铺石的前庭里生有几棵事不关己的女贞树。年前京城大将
军从他那里带走了所有剩下的中原女人,这座院子就是女人们以后的集体居住地。
这里的四面院墙围定了一处适当的私密空间,空间里有周正的中厅,平实的厢房,
厢房里有床。它看起来确实适合一些女人住在里边接待前来搞她们的男人。除了
一些很高等级的场合需要亲自送上门去让人搞,她们应该就是在这里操办了大多
数按照传说可以通过连接性器而祈使福运的神奇活动。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看起来
也很适合编写一些秘密报告。如果女人得到哪一个祈福男人的帮助,她就可以躲
在厢房里写一晚上的字,记录下所有那些她们了解观察到的消息,如果男人继续
付钱,还可以给她买到更多晚上。她们多半也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把消息传递了出
去。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的社会关系最终都是可以交易的买卖关系,中
原女人们的性关系也是一样。每一个京城居民都可以找到这座院子,按照官方的
定价付钱,而后选择一个女人把她带到一间厢房里去,连接彼此的性器官。所以
如果不是案犯们自己招供的话,他和京城大将军大概没法找到那个男人。
现在这里当然已经不再操办那些祝你幸福的生意。官方发布的公告是中原敌
国的女人已经离开京城,开始了她们第二次扬威巡游。而他按照京城将军的指派
着手处理她们的案件,他每天都会前来院中工作。沿墙整排厢房前边的花坛里正
在张扬开放的重瓣菊花是各向相异的,它们的容颜明亮但是寂静无声。他身边的
羯族女奴着落在铺石上的赤足也很安静。女奴脚镣的回响始终延续,但是因为它
的孤立、外在、和单调,可以不计入到安静中来。他们在走过整排紧闭的厢房门
扇的时候,一直可以听到一些缭绕的女人呜咽和喘息。他知道她们一直在挨打,
她们在很多使人死去活来的疼痛中,和男人寻求事件真相的逻辑理性共历了那些
时空。
他的奴隶姑娘紧走两步赶向前方去为他开门。他看到了迎门的后墙底下,从
一个较高的位置俯首、全幅、正对的女人身体。女人的赤臂合并竖举,她的手腕
被捆绑的绳索朝向屋顶牵吊得更高。女人低垂的面目前边遮挡有一些散乱的头发,
女人前倾的裸胸上垂堕的奶房疏寡,绵长,薄肉宽皮,两匹奶房浓色的软苞底下
各自拴挂有一个黑铁秤砣。每一个骑跨在一座木马的尖峭脊背上的女人,都会得
到一个憋扭,支离,裂解,模样和相貌难以名状的性器官。女人阴唇结聚处的肉
埠因为承受着重压而鼓凸了出来,她那一骨朵皱皮都遮挡不住了的蒂头肥圆臃肿,
红中泛紫的晶莹样子几乎是珠圆玉润的,她的肿胀的阴蒂被刺入了尖针,阴蒂的
根基里结扎有细绳,绳子的另头也都使用秤砣配重。这样一个重物侧挂在了木马
斜边,它也像摘花一样拈长,捻歪了女人阴蒂的肿大肉头。女人的屁股整体中立。
女人使用自己一左一右的两条光赤长腿紧紧地夹拢住了木马的倾斜侧壁,她的两
支壁立的大脚拇指根里各自拴挂的三块青砖足够沉重,能够帮助她保持住自己光
赤屁股的痛苦中立。
女人骑跨了一整个晚上的木马,就是一座平常用来摧折妇女刑犯的木马。安
装在四支高腿上的马身侧壁自下向上,从宽到窄,倾斜着支撑起来的尖峭脊梁横
行而且兀立。它深入地楔进并且扩张开一条软嫩缝隙的能力没有疑问。女人的性
器就是那条缝隙。女人自己的体重和脚趾头下的青砖重量一起,帮助她在一支坚
硬的木头楔子上极限地深切,扩张,并且充分地削磨蹂躏了自己的性器官。实际
上她已经从自己的肉唇肉户中压榨出了许多红白混杂,四处流泻开去的浆液和水。
她可能想象过一棵大白菜一样包裹紧密的、多汁多水的屄,被牛或者马那样的大
动物咬嚼开了的样子。她的遍布于女人性器软膜上的所有丝缕感触都已经极致地
扩张开放,可以使她同时体验到尖利、钝重、疾速划掠和持续弥漫的所有疼痛,
她应该已经疼得四分五裂。
男人想,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重新回来,阻挡在他的道路前边。人生是一群
猪,最终会在每一个远方遇见命定的木薯。我们可以有时地想象上树,但是我们
真正迷恋的仍然只是泥土。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开始做他命定要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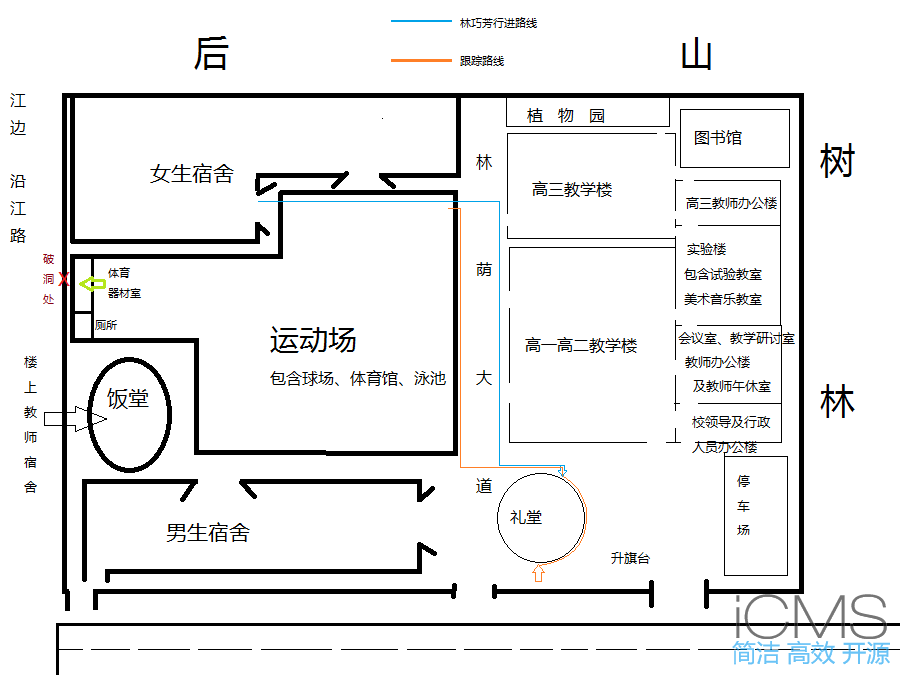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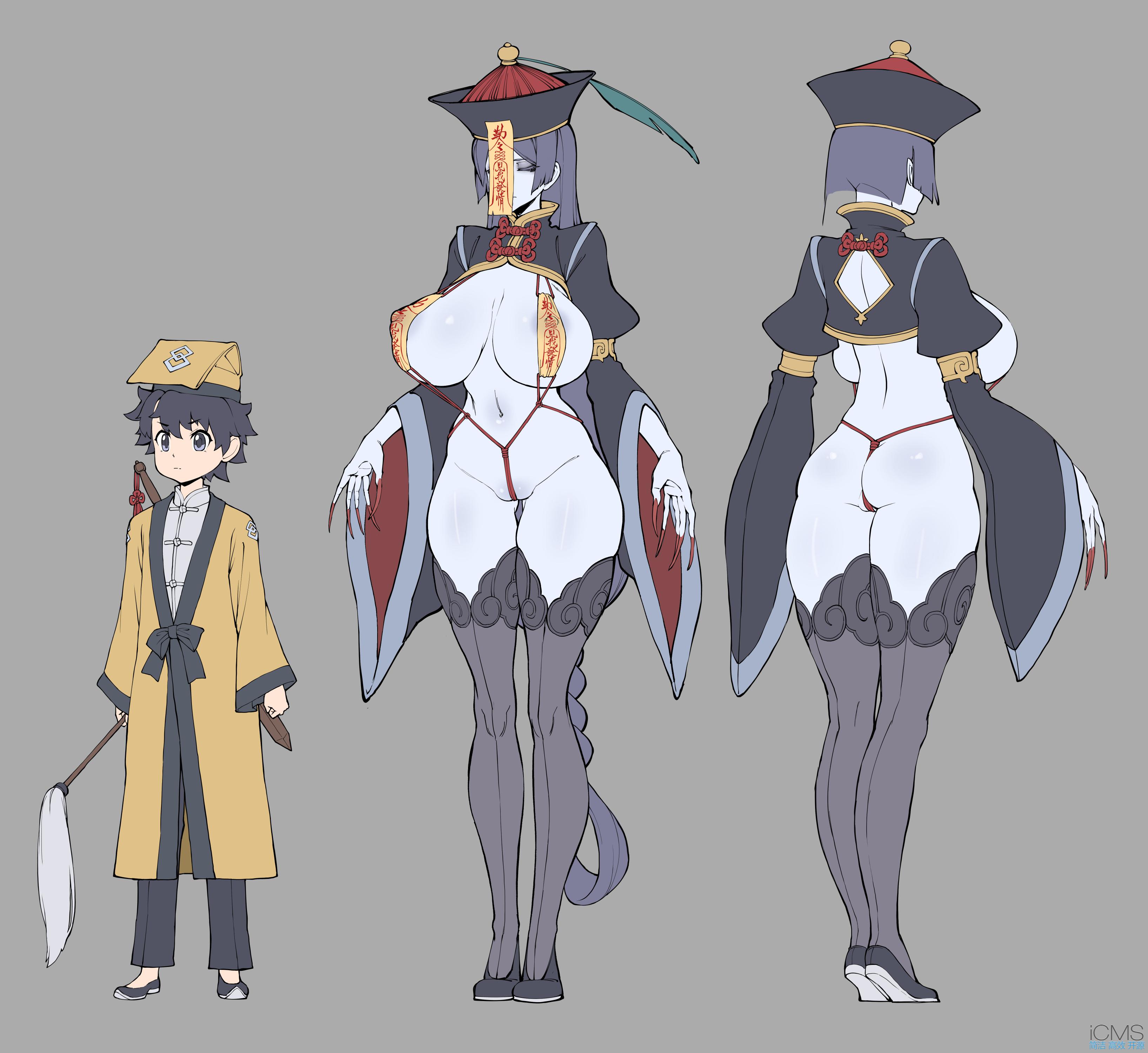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